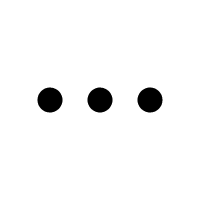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她就比同龄人成熟很多。“我不喜欢年轻的小帅哥,他们非常无趣,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她说。
她曾经是一位“个性羞涩”的模特,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她不吸烟、不喝酒,也很少去模特扎堆的派对,工作结束后总是早早回家待着。
她的模特事业也不算太成功,与“名模”的称号差得还有点儿远。
28那年,她遇到一个叫唐纳德·特朗普的男人,并且在35岁那年嫁给了他。
现在,她是唯一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任“第一夫人”的女人,除非比尔·克林顿不介意也被人这么称呼。尽管她因为在共和党提名大会上发表了一次多处“借鉴”米歇尔·奥巴马的演讲而遭人诟病,但她似乎并不介意,至少你在她毫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来。
一个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模特是如何一路杀到美国,并且很有可能杀入白宫的?这可能是美国近代最疯狂的童话故事了。
或许,梅拉尼亚·特朗普正是为华盛顿而生的。
从前不是这样的。
曾经,一名富豪迎娶他的斯洛文尼亚甜心,邀请克林顿夫妇参加他们奢华的婚宴,引来的只有媒体上社会名流版、八卦版的关注。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梅拉尼亚·特朗普感叹道。她记起过去那些“平常”的日子,带着老家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迷人的口音。

一张“有故事的”的合影
回到当时,那是2005年,唐纳德·特朗普会选择与前总统及他的第一夫人,后来的纽约州参议员一道度过快乐的时光,是很稀松平常的。“他们来婚礼时,我们还只是普通公民,”梅拉尼亚这么提醒我。
两位普通公民在属于新郎的有126个房间的弗洛里达宅邸中结婚,就是这么回事。他穿的是燕尾服;她穿的是价值10万美元的迪奥礼服,女工们耗时550个小时才手工制成,缀满了1500片珠宝,以衬托像他们这般的普通公民。一对平常的恋人,在鲁迪·朱利安尼三世与凯莉·蕾帕的见证下结为夫妇,耳畔是比利·乔尔演奏的小夜曲,在五层高的柑曼怡婚礼蛋糕的投影下,新人与宾客啜食着鱼子酱与法国水晶牌香槟酒。
那可真是一段简单而美好的时光。然而,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或许梅拉尼亚·特朗普的整个人生都不太真实——当你的丈夫筹划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而那个在婚礼上对你送上祝福的克林顿如今已经成了你的家庭不共戴天的政敌。于是你会思考,正如特朗普夫人所说的那样,实际上,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梅拉尼亚告诉我,“现在这已经成了一桩生意,跟私人情感没什么关系。”
当然,梅拉尼亚可以预见到政治会裹挟喧嚣。唐纳德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或许希望他的丈夫能够成为总统,然而梅拉尼亚——他的第三任妻子,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我们讨论这件事时,我告诉他你必须确认这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梅拉尼亚说。
我们在电话中交谈着,尽管我并不清楚她此刻身在何处。她是在特朗普大厦顶层的镀金豪华公寓吗?还是在巡回助选的途中?她总能在竞选活动中制造高潮,不过并不常常现身,似乎并没有把老公的竞选看得太重。
“没有人可以控制我。方便的时候,我就会加入我先生的行程,”她说,“在我知道我可以去的时候,并且还得确保我们的儿子不会有独处的问题。”

梅拉尼亚为丈夫完美站台
特朗普倒是时常讲起,梅拉尼亚完全能够胜任第一夫人,而这位前模特却鲜少流露出入主白宫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有一次讲过,会“恪守传统”,就如同杰奎琳·肯尼迪。在有人问起她会支持什么样的事业时,她提及自己已经涉足了很多慈善工作。“比如很多关爱儿童、对抗疾病的慈善组织,很多很多的。”
就这点而言,她与她的丈夫颇为相似,很少给出明确的信息。她会与你有眼神上的交流,刻意地重复一些积极的表态,态度友善可也有些索然无味,直到访问的人要么疑惑地试图破解她谜语一般的表述,要么就干脆放弃逼问更多细节。
然而不同于她的丈夫,梅拉尼亚矜持、礼貌,以及沉稳,接近她的人如此告诉我。“可以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平和。”她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位朋友这么说。她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异常富有,却不是社交界抛头露脸的人物;她更乐衷于家庭生活,在事业攀至巅峰后心安理得地选择急流勇退。
这种回归家庭的形象,显然不是特朗普的政敌们给她勾勒的形象。在犹他州初选时,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的盟友贴出了一张2000年时英国《GQ》杂志的封面。

British GQ 2000年1月号封面
照片上,梅拉尼亚裸体躺在一张纯白的熊皮地毯上。“看看梅拉尼亚·特朗普的样子吧,这就是你们未来的第一夫人,”竞选广告如此写道,针对的是保守的摩门教选民,“或者你们可以选择在礼拜二支持特德·克鲁兹。”
特朗普的回击充满隐喻,并且刻薄,说他也会“不小心抖出”你的妻子海蒂·克鲁兹的小秘密。接着,他在 Twitter 附上了两张并排的照片,一张是话说到一半,半张着口的海蒂,看起来就像代表邪恶势力的滴水嘴兽;另一张,是古铜肤色,碧蓝眼珠的梅拉尼亚,就像一只撩人的美狐。“照片胜过千言万语,”图片说明写道,尽管特朗普本人的 Twitter 上只写了几个字:“我的太太更辣。”
距离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流露出她的野心是成为第一夫人、而不是在家烘焙饼干因而饱受争议的90年代初期,美国已经改变了很多。然而,我们对“第一夫人”的心理预期却没有太多改观。
米歇尔·奥巴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精通法律,曾是她的丈夫在法学院时的良师益友,而如今她几乎只谈论软性话题:儿童肥胖问题,种植蔬菜。与希拉里或者米歇尔不同,倒是劳拉·布什——一位支持她的丈夫把注意力从酒瓶转向圣经的教师——最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对第一夫人的志趣。然而,这几位第一夫人试图模仿的原型都是杰奎琳·肯尼迪,无比魅力四射,以及对自己丈夫的沾花惹草无比容忍。

梅拉尼亚的学习榜样杰奎琳·肯尼迪
认识梅拉尼亚的人说,把杰奎琳视为榜样对她而言并不是个过分的想象。“她很善于挑选瓷器的图案;她会成为典型的第一夫人的,”时尚造型师菲利普·布洛赫说,他与特朗普夫妇都有合作,还与梅拉尼亚一起出席过时尚秀。然而与杰奎琳不同的是,杰奎琳结识约翰·肯尼迪时,她未来的丈夫已经是国会议员,梅拉尼亚在1998年认识“花花老公子”唐纳德·特朗普时可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政客的伴侣。
梅拉尼亚所畅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熠熠闪光的生活,她在 Instagram 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一切,也发布 Twitter,直到一年之前。那时她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后突然陷入了沉寂。估计是有人提醒她还是关上这些似乎永远在炫富的账号为妙。在她发布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在浴室金色镜子前的自拍。“再见了,我要去我的夏日别墅了。”
尽管梅拉尼亚很是享受一位厨师与一位助理为她提供的服务,却没有雇佣保姆来照顾他们的儿子,巴伦。那是身为母亲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很明白各自的角色,”梅拉尼亚有一次告诉 Parenting.com,谈及了自己与丈夫的分工。“我不会让他换尿布,或者哄巴伦上床。”那个她口中的“小特朗普”将来想要成为“商人和高尔夫球手”,如他的母亲所言,他总是穿着西装。“他不是穿运动裤的小孩,”她说。

梅拉尼亚这几年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儿子巴伦身上,因为她和特朗普的分工很明确,她绝不会让丈夫给儿子换尿布,因为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儿。
梅拉尼亚是个讲究的母亲,也是个讲究的妻子,对此特朗普颇为欣赏。与她相处很轻松。“我一天到晚努力地工作,”唐纳德在2005年时告诉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我可不想在回到家后还要经营两人的关系。”对已经离过两次婚的唐纳德而言,梅拉尼亚简直不能更美好了。他从没听过她放屁,或是见过她大便。(梅拉尼亚曾说过,她的婚姻成功的关键是分开使用的浴室,而且她会做好避孕工作完全不让老公操心。)
他有一次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跟主持人霍华德·斯特恩吹嘘:她就是如此迷人。她有着完美的身材——5英尺11英尺高(约180公分),125磅(约57公斤)——傲人的乳房,绝非什么俗物。斯特恩反问特朗普:假设梅拉尼亚遭遇惨烈的车祸,左臂没了,眼角撞烂了,左脚变形,唐纳德还会对她不离不弃吗?
“胸部还好吗?”特朗普问。
“胸部没问题,”斯特恩答道。
“那我肯定不会离开她,”特朗普骄傲地回答道,“胸部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你在说什么?”
除了家庭之外,这对夫妇鲜有相同的热情。梅拉尼亚涉猎时尚设计行业。她在 QVC(全球最大的电视与网络百货零售商)上首次发售的珠宝与手表在45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
在她的珠宝生意刚起步时,梅拉尼亚自己画草图,展现了她在绘画上的天赋。她童年时的朋友告诉我,她还是个孩子时就显示出了这方面的才华。梅拉尼亚的高中同学佩特拉·赛迪说她非常有天赋。但我在斯洛文尼亚遇见的她的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朋友却有些不同的看法。
“人们都说她很聪明,她像杰奎琳·肯尼迪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那位朋友停顿了一下,试图找出合适的词汇。“在她感兴趣的事上,她十分聪明,比如说珠宝。她并不笨,绝不是无知的人,只是她也不是特别聪明的那种。”
在梅拉尼亚的想法中,特朗普的白宫理想跟她没有太大关系,那些极具争议的观点也与她无关,比如对移民的蔑视,尽管她自己在2006年时才刚刚成为美国公民。“我不想跟政治或者政策扯上关系,”她告诉我,“那些政策什么的是我丈夫的工作。”她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会跟特朗普分享。“现在没有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她提及自己给丈夫的建议时这么说,“因为那只是我和我的丈夫之间的事。”
她只是给出作为妻子的建议。“她总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布洛赫说,“如果特朗普问起,她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她也绝不会开口谈什么。”
弗拉迪米拉·汤姆西克与梅拉尼亚是同学,也是他们家的朋友。汤姆西克告诉我,她的成长经历奠定了她对婚姻的看法。“特朗普会选择她的秘密在于——”她解释道,“她传统的价值观和对家庭的重视。”换句话说,那张在地毯上裸着身子的照片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幌子:梅拉尼亚是传统眼光中理想的妻子。实际上,她是非常正统的——特朗普的完美“贤内助”,正如圣经中对艾娃的描述。梅拉尼亚·特朗普几乎是为唐纳德定制的,就好像一场神圣的手术从他的身体上取下肋骨塑造的她。
他第一次遇见梅拉尼亚——在1998年秋天纽约时尚周期间的一场派对上——唐纳德·特朗普那时已经52岁了。他傲慢,并且打扮得花里胡哨,惊人的富有,堪称纽约传奇。梅拉尼亚当时28岁,身材高大,一头咖啡色的长发,羞涩,面部紧绷,眯着眼睛,好像摄影机捕捉到的总是她临打喷嚏前的一刻。“我不太知道唐纳德·特朗普,”她如此形容,“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我从没关心过唐纳德·特朗普以及他所过的那种生活。”

梅拉尼亚曾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模特,事业并不算太成功。
几年前,在米兰和巴黎当模特时,梅拉尼亚·诺斯(Knauss)按照德文的拼法稍稍改动了自己的名字——把 v 改成了 u,又加多了一个 s。她在欧洲的发展十分顺利,不过算不上超级名模,于是打算前往美国精进自己的事业。保罗·扎波里把她带到了纽约的一场模特大赛,还给她办妥了工作签证。
扎波里是个意大利富商,在纽约有着各式各样的生意,但具体做的什么,又有些神神秘秘。有时,为了推广自己手下的模特们,他会把女孩们带去一些场合,同时也邀请来摄影师、制作人和富有的花花公子们。
1998年9月的那个夜晚,扎波里邀请了特朗普。他是带着自己的女友来的,但很快就被梅拉尼亚吸引了。把自己的女友打发去洗手间后,他有了几分钟与他中意的模特搭讪的机会。然而梅拉尼亚知道特朗普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很快就从他在派对上的表现得到了证实,他是带着女友来的,现在却在问她的电话号码。
她拒绝了。相反,她问特朗普要了他的联络方式。这位亿万富翁本身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梅拉尼亚还在观望,就像金币总要拿来用牙咬才能一辩真伪。“如果我给了他我的电话,那么我就只会沦为他的玩物之一,”她如此回忆。
或许梅拉尼亚的回避引起了特朗普的兴趣。实际上直到一个礼拜后,她才给特朗普打电话。“我对‘追星’什么的没有兴趣,”她解释,“我们之间很来电,很有感觉,不过我对‘追星’没兴趣,或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
梅拉尼亚与特朗普交往不久后,她就提出了分手。“刚开始时,她有彼此信任问题,”马修·安塔尼亚说。安塔尼亚是摄影师,梅拉尼亚刚搬到纽约时住在联合广场附近的泽肯多夫大厦,两人是室友。“她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他又回到了老样子。她一直都保留着自己的公寓,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不到6个月他们又复合了。如果不是她调教了唐纳德——他坚称自己对梅拉尼亚绝对忠诚——就是她接受了唐纳德善变的个性。在所有的访问中,梅拉尼亚都表示她无意改变特朗普。她在特朗普身上寻找到的——除了年龄上的差距和足以吓跑大部分女性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她渴慕已久的东西。“权力欲与保护欲,”来自卢布尔雅那的一位梅拉尼亚的旧友告诉我,“我想她需要一位强势的男性,一位像父亲般的人物。”

“你在说什么?”以及“我驯服了这个男人。”
如今,梅拉尼亚在斯洛文尼亚显然口碑不算太好,因为人们觉得她忘本。有传言说,她拒绝讲斯洛文尼亚语;唐纳德只来过她的家乡一次,并且只停留了一顿饭的时间。人们怀疑梅拉尼亚以出生于斯洛文尼为耻。不过在访问中,梅拉尼亚从没有对自己在斯洛文尼亚度过的日子有任何躲闪;也不为此觉得尴尬。“我很怀念童年,”她告诉我,“那是非常美好的经历。”她的儿子说一口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他用斯洛文尼亚语与外公外婆交流,后者已经移民到了美国,就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然而对梅拉尼亚而言,斯洛文尼亚只是她个人经历中短暂的篇章,这个国家很快就不能承载下她事业发展的野心。
梅拉尼亚·诺斯在1970年出生时,塞夫尼察只是个铁路小镇,距离首都约1小时车程。虽然是共产主义政权当政时期的清贫日子,与其他人家相比,诺斯家过的相当宽裕。梅拉尼亚的母亲阿玛里加·乌尔克尼克在一家儿童制衣厂设计图案。她在1966年时结识了维克托·纳夫斯,当时他是邻近城镇市长的专职司机。

梅拉尼亚的父亲维克托·纳夫斯与母亲阿玛里加·乌尔克尼克
在那个年代,斯洛文尼亚还是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一员,人们的生活拮据,但阿玛里加的穿着总是很讲究,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她非常漂亮,”汤姆西克说,如今她在当地运营着一间医院,梅拉尼亚在嫁给特朗普后给医院捐赠了2.5万美元。“她真的十分迷人。”阿玛里加下班后,总是给自己以及一对女儿伊内斯和梅拉尼亚缝制衣服。在梅拉尼亚学会画画后,她会描出自己设计的草图,再由她的母亲或是姐妹缝制出来。梅拉尼亚还制作自己的首饰。“梅拉尼亚从不穿从商店里买的衣服,”她的一位朋友回忆。
这一家人还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相片,前往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度假。在他们塞夫尼察的公寓里,每间房间都刷上了丰富的色彩——客厅是蓝色的,厨房是红色的,梅拉尼亚的房间是黄色的。因为工作出差去了法国和德国的缘故,阿玛里加带回了各式色彩的画儿,这在南斯拉夫很少见。她还带回了西方的时尚杂志,梅拉尼亚的朋友们总是看到她在翻阅它们。“他们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梅拉尼亚童年时代的朋友米莉娅娜·吉兰克里克回忆。(她如今是之前她与梅拉尼亚一起念过的那间学校的校长。学校里正在讨论要设立一场特朗普夫人的永久展览,作为这间学校最知名的毕业生。)
吉兰克里克记得,梅拉尼亚的父亲维克托每个礼拜六都会心怀爱意的清洗自己的那辆古董奔驰车——当时的另一种稀缺品。“那就好像一场仪式,”吉兰克里克告诉我。结束了给赫拉斯特尼克市长开车的工作后,维克托成了一间国营汽车公司的销售员。1976年的文件显示,维克托曾被怀疑进行非法交易和逃税漏税。(他曾因税收违法行为被起诉,尽管他在后来的记录中是清白的。这跟斯洛文尼亚本身的历史也有关系,法院对我的解释是“法律平反”。)梅拉尼亚设法阻止了我与维克托谈话,还否认了曾进行过有关调查。“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调查,也从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她的语速很快,“我们的过去很清白,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在卢布尔雅那为汽车公司服务时,维克托在那里有一间公寓,是整个城市中最早开发的高层住宅。它位于黄金地段,为两个女孩提供了在首都生活的地方,以便她们入读设计学校——另一件奢侈品。同时,在塞夫尼察,当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工厂分配的乏味公寓中时,维克托在城镇里最时髦的地段建起了一栋自己的房子。
“特朗普令我想起维克托,”维克托的朋友和邻居托马斯·杰拉告诉我。“他是一位销售员,靠自己的人脉做生意。”如今在塞夫尼察,维克多和阿玛里依旧拥有着自己的房子,每年会回来两到三次。
事实上,如果你把维克托·诺斯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照片摆在一起,你不会为两人间的相似之处而震惊。唐纳德仅年轻他的岳父5岁。两人都身材高大,发福的男人顶着金色的头发,总是穿一身亮丽的西服;他们都是傲慢的男子,喜欢享受生活中的好东西。“他很注重品质,”梅拉尼亚说。“维克”——他的朋友们大多这么叫他——“喜欢好东西,”杰拉告诉我。“他喜欢车子。”他跟很多人一样,向我提起维克托昂贵的奔驰车收藏。“你绝不会看到他驾驶其他品牌的汽车。”
那些认识维克托的人透露,他的脾气暴躁而且倔强。“他天生就会讲笑话,”诺斯家的邻居和朋友安娜·吉兰克里克告诉我,“如果他去酒吧,人们都会注意到他。”维克托很能调动整个房间的气氛,她说。“他总是强势的那个人,阿玛里加很支持他。她是完美的母亲和太太。”
相当多认识诺斯家的人都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他们是典型的斯洛文尼亚家庭,”医院负责人汤姆西克说。“他们很传统,家人间的关系很好。”维克托的朋友们总是带着钦佩之情谈起这位名声不错的精明商人。另一位维克托的朋友告诉我,“他是个商人,总是趁机行事。”
对于她的丈夫与父亲之间的各种比较,梅拉尼亚倒是表达了他们的确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很勤奋,”她说,“都很聪明,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但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有着相同的传统。我与我的丈夫很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父亲也是。他是个以家庭为主的男人,有他保持的传统。他很勤奋。我的丈夫也是。”
与特朗普一样,维克托不仅只是个工作勤奋且乐衷投资房地产的商人;一旦涉及女人,他的故事复杂了起来。维克托还是个司机的时候,在他迎娶梅拉尼亚的母亲前,他在城里认识了名叫玛丽佳·西吉贾克的女人。他们约会了一段时间。1964年9月,她告诉维克托她怀孕了。根据西吉贾克在法庭上的证言,维克托提出会娶她,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要求她去做引产手术。这是因为——维克托说,孩子不是他的。1965年5月,一名男婴出生了。三个月后,玛丽佳向维克托提出孩子抚养费的诉讼。维克托一直拒绝履行作为父亲的义务——法庭上的相关记录巨细无遗,从他与玛丽佳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到她的例假周期——要求法院进行血液比对。根据医学检查的记录,法庭确认维克托正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维克托为了拒绝支付抚养费一路把官司打到了斯洛文尼亚的上诉法院。法院的判决总是有利于玛丽佳的。(法庭记录显示维克托迟交了上诉申请——还厚颜无耻地撒谎,给出的延迟理由完全无法令人信服。)
维克托从没有与这个孩子相认。丹尼斯·西吉贾克如今已经50岁了。他是梅拉尼亚同父异母的兄弟的事实从没有在媒体曝光,尽管他对传媒三缄其口,但亲口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并且允许我从斯洛文尼亚档案馆中取回了相关的法院文件。
他住在赫拉斯特尼克的一栋狭窄的公寓里,他那曾经在玻璃厂工作的母亲几年前在这个地方去世。她再没有嫁人,也没有生更多孩子。丹尼斯说他没有见过父亲的印象。维克托在孩子18岁之前支付了抚养费,之后就彻底在他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我从没有说过,‘嘿,爸爸,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这个春天,丹尼斯在他家的客厅里告诉我。时不时的,丹尼斯会听到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不过他说很害怕联络他,担心打扰诺斯家的生活。如今,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从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想要从他的父亲或者特朗普那儿得到些什么。他不介意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们伊内斯与梅拉尼亚见面,尽管他相当确信她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当我在电话里向梅拉尼亚提起这件事,她否认了事件的真实性。在我把斯洛文尼亚法院的文件传送给她后,她后来答复原先没有理解我的问题,解释道,“是的,我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些年头了,”她补充,“我的父亲是个注重隐私的人,请尊重他的个人隐私。”)
每个在梅拉尼亚小时候就认识她的人都记得她是多么得引人瞩目。“她的美貌很特别,不是典型的那种,”一位卢布尔雅那的朋友告诉我。“她有一双迷惑人的双眼。当你望向这双眼睛,就好像望着某种动物的眼睛一般,很容易被吸引住。

梅拉尼亚为英国《GQ》拍摄的大片
史丹·杰尔克是在1987年时最早拍摄梅拉尼亚的摄影师,后来与她有过多番合作。他的看法与那位朋友相似。他是在卢布尔雅那的一场时尚秀上见到梅拉尼亚的。当时她正在等自己的朋友。她的身形消瘦,羞涩,留着一头长发,眼神熠熠。他建议梅拉尼亚来自己的工作室。对此,她好像没什么兴趣,他记得。“上学才是对她来说最要紧的。”
然而,一个礼拜后,她来了。头发扎成了少女那样的马尾辫,还带来了各式各样自己的衣服:打底裤、紧身衣、高腰酸洗牛仔裤,一件看起来像柳条编织袋的无袖毛衣。她很内向,紧张,但照着杰尔克的指导,很快就掌握了摆 pose 的方法。在照相机前,他看到了梅拉尼亚的未来。

1987年还只有16岁的梅拉尼亚就已经略显成熟。
几个礼拜后,她回来了,杰尔克拍摄了一组黑白快照。照片里,16岁的梅拉尼亚·诺斯穿着服饰目录上一些衣服,光着脚丫。“我没有找到适合她的鞋子,她的脚非常大,”杰尔克说,大概要穿9码的鞋。“其他模特的脚都比较小。你知道在斯洛文尼亚人们怎么形容脚大的人吗?”杰尔克问,咯咯笑了起来,“脚大吃四方!”
那些日子,梅拉尼亚并没有想着要当模特,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设计师。她向本地一所大学的建筑学院提交了申请表,成功通过了入学考试。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些年,她十分专注学业。她不喝酒,不去派对,不抽烟。甚至在她认识杰尔克开始自己的模特生涯后,她还是习惯在工作结束后早早回家,跟个性安静而且内敛的姐妹相处。
“她很习惯独处,是个不合群的人。拍摄或是走台结束,她总是回家,而不是外出。她不想浪费时间在派对上,”杰尔克记得。
“那时候的男孩们更喜欢派对女孩,但我们不是那种,”佩特拉·赛迪说,她是梅拉尼亚那时的同学。相反,她们总是会去梅拉尼亚或是佩特拉的家中,“喝果汁或者聊天。”另外一位卢布尔雅那的朋友记得,梅拉尼亚“在那方面有些特别。她很享受两人、三人或四人的相处。她不需要更多人的陪伴。”
那些对梅拉尼亚有印象的人还记得,在她的同学们满脸粉刺,穿着校服的年纪,梅拉尼亚总是打扮得相当精心,赛迪回忆到。粉底、睫毛膏、刷子、唇彩,一切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即使是在夏天,她的外形总是那么完美,每天都是如此。
大学时,梅拉尼亚曾与一位同样是模特的男孩约会过,男孩念的是体育系。然而,她对男孩表现出来的随意相当不满。他是个帅气,直爽的20岁男孩;她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追求的不仅仅是嘻嘻哈哈的校园式浪漫。这个男孩无法提供梅拉尼亚所需要的,这令她十分失望。“她很敏感。她想要更多。”另一位那个时代的朋友回忆,“我们都是20岁的年纪,不过她要成熟得多。”

年轻的梅拉尼亚面部表情远比现在丰富
1992年——那一年,梅拉尼亚赢得了斯洛文尼亚年度模特大赛的第二名——不仅是卢布尔雅那,甚至刚刚独立的斯洛文尼亚都已经无法容下她的野心。而南斯拉夫更大的市场——约有2400万人口——则已经四分五裂。待在这个狭窄的仅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意味着她模特生涯的终结。要去一个更大的舞台,从事真正的模特事业,她需要离开。“她很清楚,斯洛文尼亚已经没有任何她留恋的地方,”一位来自卢布尔雅那的朋友说,“她想要走。”
在大学念了一年书后,她成功休学,前往米兰。至此,她与家乡的联系愈发淡薄。她回来卢布尔雅那时,赛迪偶尔会与她见面,但很快又失去她的音讯。几年前,她的高中20周年聚会时,赛迪和她的同学们给梅拉尼亚写了信。他们给梅拉尼亚的代理人发送了邮件,在她的 Facebook 上留言,但从未收到任何答复。“她切断了与这里人们的联络,”来自卢布尔雅那的朋友说。“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全部在这里发生的都留在了这里。”
梅拉尼亚在米兰和巴黎的发展相当顺利。1996年,她结识了扎波里,后者设法解决了她的工作签证,帮她报名了纽约的模特大赛,她怀着更大的梦想迁往纽约。
然而梅拉尼亚——尽管当时她刚年仅26岁,就已经面临了模特的年龄危机。“那是个令人困扰的年纪,20多岁的最后几年。模特行业对这个年龄的女孩可不怎么友善,”她的前室友安塔尼亚说。扎波里的经纪公司依据合同支付她的房租。“她有时会谈及工作上碰到的烦心事,”安塔尼亚回忆。她总是抱怨为什么这个或那个摄影师选了其他人而不是她,那些更年轻的姑娘们。“她并不是每天都有工作,”他补充,“她每天都去试镜,并不是每天都有收获。她说欧洲跟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她要吃香得多。”梅拉尼亚有一段时间十分艰辛地维持着自己的生计,担心属于她最好的年代已经离她远去。
在愈发冷漠的市场反响中,梅拉尼亚寻找着她的优势。她开始尝试试镜一些酒精和烟草广告,其他年轻的女孩由于年纪太小无法接到这些工作。有一次,她登上了骆驼牌香烟的广告,巨大的广告牌就立在纽约时代广场。她也在其他地方寻求突破。“她声称去度了两个礼拜假,回来时,整个人都更——红润丰满了,”安塔尼亚说,试图在脑海中搜寻合适但又不冒犯的语汇。“她向我坦白过。她说她没有其他选择,她想要接更多内衣广告。”

梅拉尼亚拍摄的不知名杂志的封面
我问她是不是隆过胸,再一次地,梅拉尼亚笑出了声。“我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她说。“很多人说我在脸上动了很多地方。但我真的是原装的。我过着健康的生活,保养自己的皮肤和身体。我反对使用肉毒杆菌,反对注射美容。我就是这样优雅地老去,就跟我的母亲一样。”
在纽约,梅拉尼亚过着安静的,以家为中心的生活,健身护肤一样不少。她很少去派对,从不带任何人回家,而且绝不晚归。“她从不去跳舞俱乐部;她会在晚上10点去希普利亚尼吃晚餐,在凌晨1点前回家,”安塔尼亚回忆。“她约会的男性大多富有、勤奋,有欧洲人的做派。他们大多是意大利人,花花公子们。他们会一起吃晚餐,但她回家总是比我早。”
这一次,又是扎波里,那个在1998年向她伸出橄榄枝的男人——邀请她前往小猫俱乐部,无意中使她得到了一位花花公子的电话号码,将她送上了——谁知道呢——或许是通往白宫的大道。
尽管多数时候,她都是丈夫身后不出声的女人,在过去那个漫长和有些异样的冬季初选巡回拉票中,与丈夫共同出现在多个场合。梅拉尼亚的初次助选是在四月飘雪的威斯康辛州。我也在那儿,看着她在丈夫热切的陪同下登上舞台。“她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爱自己的儿子巴伦,爱极了,”他说,“我必须要说,她会成为无与伦比的第一夫人。”人群沸腾了。“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太太——梅拉尼亚,”他说,“来吧。”

相当顺从地,她踩着令人晕眩地克里斯提·鲁布托高跟鞋,身穿海水泡沫色的夏日连衣裙,如同一只长腿娃娃一般,登上舞台。虽然尚未及夏日,她的肤色已经晒得古铜,对自己身处的角色游刃有余:别人眼中的美人。
她开始读着已经在讲台上准备好的发言稿,一连串对她的丈夫的赞美。“他很勤奋。他很善良。他心地很好。他很聪明。他非常善于沟通。他是位优秀的谈判者。他从不说谎。他是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很光明磊落。”
演说词——都很简短,由陈述句构成——听起来就好像是她的儿子写的功课,但很快就进入了课间谈话的节奏。“或许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如果你们攻击他,他会加以十倍的奉还,”她提高了音量,语调坚定,迎来了狂热的掌声。“不论你是谁,男性或者女性,他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或许在一年前,梅拉尼亚对这一切毫无兴趣——不想要她的丈夫投身选战,不想要被人打探各种私隐,不想要成为一位政客的妻子。然而如今她站在这里,对生活呈现的崭新面貌迈出阔步。她微笑起来,面部有些紧绷,就像一头狮身女怪,注视着面前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