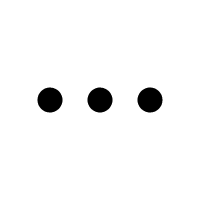2008年左右,小飞离开了《Miss格调》,专职做助理。一开始单打独斗,后来活儿越来越多,他开始叫身边朋友来帮忙。起初只是心想让有些没工作、或者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并且有车的哥们顶个场,但之后小飞觉得活儿挺多,一个月下来挣得也不少,干脆自己领个头,带着大伙一块干就成了。
2008到2013年几乎是中国时装杂志最鼎盛的年代,广告销售经理们总有签不完的订单,随之而来的别册、软文需要大量编辑负责拍摄的内容。此外,各本杂志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也是鼓足了劲儿奔赴在赶英超美博门面的路上:大制作、大明星的拍摄络绎不绝,对助理的需求更是旺盛,你可能听说过那些拿着微薄酬劳却干着最辛苦的体力劳动的助理们,因为一些意外问题被编辑骂到精神失常的故事——那是中国时装编辑们最耀武扬威的日子。
大部分杂志助理都是在校生,流动性大且经验不足,往往好不容易被“调教”出来,又因各种原因离开。小飞则不然,他的“助理公司”旗下的人,都经过他一手培训,从跟品牌发邮件借衣服、跟踪整理、片场跟拍到后期还衣样样在行——“小飞的助理们都挺好的,用他我放心,就是价钱有点贵,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大拍摄时找他。”某时装刊物的时装总监说。
“一开始一个活儿就是是行价,300,后来油钱、物价涨了,我们也跟着涨了,从500到800。那时候杂志的活儿多,我这好点的助理一月能赚万把块,差一点的5000来块。我自己干的少了,主要就是给他们统筹安排工作,再接着开始收一个所谓的份儿钱,每人500,一来就当大家给我一工钱,二来我琢磨着用这钱大伙儿谋点新事儿干干,因为已经有点规模了。我们最后买了一金杯,也雇了司机,但结果发现没什么大用,就给卖了,不过算是没赔没赚。”

当“助理公司”头目的日子里,小飞的生活很辛苦,满脑子都是样衣、快递、人员安排,一睁眼就是大量的电话、短信:“基本晚上都得一两点睡觉,可能睡不了俩小时就得起床,有一次我出错就是因为睡过头了,(康乐)康老师本来约好让我早晨去机场接他,他那次出差回来拿了好几箱东西,但我起晚了,后来玩命往机场赶,路上我跟康老师打电话道歉,他说你不用来了我自己打上车了,我知道他不是小心眼的人,但这些年为这事儿我还是挺自责的。”
“不过多晚我都会回家,因为我只要回去了,我媳妇才能安心,”小飞的太太算是她的发小,俩人因为一次拍摄相识,“有次拍美容片,得让模特剪短发,我找了多少个姑娘都现场一听就都跑了,后来把我媳妇找来了,没想到她一听特痛快就答应了。再之后《Miss格调》办了个类似相亲会的活动,我叫她也去了,现场有人跟她搭话,我说对不起这是工作人员,不参与此次活动。”
小飞工作室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流行,时装杂志的好日子逐渐成为过去,小飞开始为“助理公司”的未来踌躇,但天道酬勤,在过去几年积累的业内口碑给了他第二次转折:“我得感谢原来Loewe的Alice(现任某精品皮具集团北京区公关人员),Alice大姐一直向上海总部市场和公关部门那边力荐我,让我赶上了Loewe这个客户。那时候编辑之间不得老自己转衣服吗,这家用完了转下家杂志,有时候还得转给明星经纪人,其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另外一般品牌、杂志用的普通快递也不管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送到就完了。送丢了也是常有的事儿,或者一开箱发现少了东西,但双方都说装的时候没问题。”
小飞所说的样衣丢失,正是杂志编辑、品牌公关的噩梦。大部分品牌面临和杂志一样的问题,做最基础、也是最复杂工作的样衣小弟小妹流动性大,而有些品牌也因为在华规模较小,甚至不具备专业的样衣间和相应人力。如何保证能为在京数目较多的媒体、艺人提供品牌新款时装从而提升曝光率,同时避免丢失,一个做中间协调的第三方样衣间需求诞生了。
“Alice的推荐下,我接了第一个客户Loewe,他们把样衣都放在我这,编辑和经纪人跟他们邮件沟通借衣后,客户会把邮件转给我,我在从中协调怎么给人送,还有拿回来的事儿。因为也干了这些年嘛,这圈里的人都算认识,做起来也还成,当时一个月给我的服务费是5500元,我找外面开个发票花500块的点儿钱。还有你知道Fendi不是把样衣直接放在店里让店员拿给编辑嘛,结果他们丢了一次店货,店员抱怨肯定是自己去库房拿样衣时店里人员不够才闹出丢东西的,后来他们也找到我,把样衣放在我这了,我给编辑送,等他们拍完再拿回来。一茬接一茬,Dolce & Gabbana有次做新品预览,他们人手特别少,新衣服到了还得整理熨烫、按照规定搭配,根本忙不完,问我能不能来帮忙,我说可以就接着聊费用,他们说香港那边的老大决定按一天100给我,整个下来七天700块,我开始想这太低了,但琢磨下就当是赚个人情赚点名声吧”。
Dolce & Gabbana的预览完成地非常顺利,小飞过往的人脉积累甚至能充当临时公关的角色,这让他获取了甲方的信任:“后来他们又找我,我就说咱能不能涨点钱,Dolce的姑娘说没问题,我们老板指名道姓要你来,说小飞很重要。”
“慢慢做久了,有些品牌的人跳槽到别的品牌了,也会找我继续做。”如今,小飞服务的客户扩展到了Celine、Gucci、Bally、Saint Laurent Paris,KARLA OTTO,MaxMara等,也有晚辈开始尊称他为“飞哥”了。他注册了公司,取名“F.Center飞盛思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给员工上了五险一金,在东四环租了一处300多平的工作室,一半用作样衣间,一半用作摄影棚。年迈的父亲平时也在这里,老爷子气度不凡,也算沾了儿子的光,几乎所有涉及老男人主题的时装片,小飞他爸都客串当模特拍过了。
“客户多了嘛,得公对公了,得有正规发票。”现在,单个品牌付给他的服务费已从当年的四位数上升到了五位数,算上客户总数,小飞的收入今非昔比。对品牌而言,这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因为就像之前在做助理时得到的评价一样,小飞让人放心。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小飞也遇到过棘手问题,结果导致他失去了一个顶级品牌客户:“有次把东西送回品牌那,他们说少了一件东西,但我们都是有过清点登记的,后来交涉过程中我听说品牌认为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员工拿走了,但我绝对相信我的同事不可能这样做,接着品牌就不和我们合作了。”
“你哭过吗?”回想起我见过的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儿便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助理们,以及就连我这个自诩不爱哭的人,也曾有被冤枉后眼红偷偷抹鼻子的经历,眼前这个对自己和同事要求极高的前辈想必也有过。
“哭过,就是因为那次丢了客户的事。”那次事件后,小飞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抹眼泪——他的手不大,挺厚实,习惯了整理堆积如山的样衣,也有劲儿搬整箱整箱的重物,但用来抹眼泪却不多。“我心里有点委屈,给媳妇发了微信,媳妇一劲儿安慰我——嗨,但我知道我还得自己消化这事儿,这些年就哭过那一次。”
真金不怕火炼,小飞的业务持续进展,陆续还有几个顶级品牌将要进入他的客户名单,甚至他还想扩充在上海的业务。这个既不是公关公司,也不是快递公司的第三方样衣间,在夹缝中生存得游刃有余。时装杂志或许没落了,但只要零售还在,这些品牌还要在中国用样衣做媒体、名人推广,那么小飞的买卖就能继续。
尽管没受过多么高的教育,但小飞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他对工作一样质朴又智慧,他七岁的女儿漂亮得让平日极为谦虚的小飞自己都不羞于称赞:“随她妈妈,你看我这样是拿不出手了,但我闺女能见人。她妈脾气不好,总说她,我就跟我媳妇说你瞅,咱们姑娘一直在学怎么做个更好的女儿,你也应该学着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有阵子我去接我姑娘放学,我一般把车停在离学校远点的地方,不是怕同学之间攀比家长的车啊,我是想和我姑娘走会路,就跟我小时候家里来接似的,因为平时忙,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我说就算你长大了给我带回来一个女孩也没所谓,爸爸会学会分享你的幸福。”

当然,我们不能免俗地聊了聊关于小飞工作室的未来:“我也想过有个更稳定的靠头做大些,这样我们就能显得更正规啦,比如登记样衣的公司信纸,全都是印着公司Logo的好纸。现在咱毕竟还是小,在这些环节我能省还是得省着点。之前也谈过一些类似的合作,可觉得还是不成熟。”
整个聊天的过程中,小飞接了9个电话,手机屏幕上排满了微信通知,但出于礼貌,他几乎没碰过手机,我知道不能再耽误他的时间了。
“你怎么来的,开车吗?”临走时我问。
“没,我骑工作室的电动车来的,这个快”。
“你们还有电动车呐!?”
“汽车、电动车都有,都有用”。
没有必要感谢小飞,因为他不是这个行业的雷锋;也并不想在结尾再度说尊敬小飞,因为说了跟没说一样。可倘若是换成一下这番话,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反对:
我们都爱小飞。